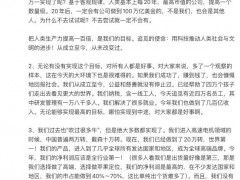一点点微小的关心和共情可能有巨大的能量。
林子发布了一条新的群公告。
“大家,群主出于个人原因考虑,本群将于4/30解散。请大家保存群公告里的购药渠道以及添加昭阳大药房、嘉会医疗、浦东曜影医疗等工作人员微信,以备不时之需。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在群内相互帮助。大家多保重。谢谢。”
这段文字下面,附上了她整理好的购药与问诊渠道,平台链接、配药和开处方的流程都详细注明。
这个群的名字,叫“上海抑郁症药品互助”,4月15日组建。4月21日,曾参加《乐队的夏天》的音乐人张守望在微博贴了群的二维码,经他扩散,群里很快加满了500人。第二天,林子又拉了二群,两个群共接纳了700多名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患者的求助信息。
“为什么要解散?”有人问。
“群里面的渠道搭起来了,京东、叮咚、美团线上药房也慢慢开始有了。(订药渠道)已经开始有恢复的迹象了,我们觉得群就没有必要长期保留了。”林子说。于她而言,半个月里,这个群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,但解决问题、互相支撑的精神,是始终进行着的。
一天的药掰成两半吃
林子家在上海浦东区,参与线上志愿,是从4月初开始的。原定于4月5日解封的浦西,突然被通知延长封控,解封时间未定。很多人家里没囤够物资,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林子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,和朋友、其他志愿者一起做了一个“紧急配送”群,协助采购物资,为缺少食物的市民提供配送服务。
一周过去,林子看到,食品需求的口子渐渐能被团购或政府分发的少量物资稍填上些了。这类需求的紧急程度降下来之后,她想,肯定还有更需要被关注的紧急状况和细分群体。
4月15日下午,林子点开“我们来帮你·上海抗疫互助网站”(daohouer.com),埋头翻了80多页。网站上列着用户上传的求助信息、联系方式,并标注了求助的紧急程度。据媒体报道,截至那天,共有4216人在网站上发布了求助信息,7%已解决,53%跟进中,39%还待解决。
林子发现,还有不少人缺抑郁症缓释药,说买不到。也有人留下信息,说手里的药有余,可以分给需要的人。
林子决定来担任连接两头的桥梁。她随即加了网站上一些求助者、援助者的微信,15日晚上和其他几位志愿者一起拉了“抑郁症药品互助群”。
上海疫情期间,精神类疾病患者状况如何?三月底四月初,疫情封控政策的突然变化导致物流渠道几近停摆,线上药房的快递很多也发不出来了。很多人因长时间闭门不出而出现严重的焦虑,没来得及备药的患者不得不靠降低药量来延缓断药。
“比较艰难的时候,一天的药需要掰成两半吃,夜晚难以入睡,早晨难以起床,无法集中精力居家办公,对以往的兴趣爱好也提不起兴趣。”一位群内的抑郁症患者告诉《中国慈善家》,“头痛、胸闷、心悸,也不知道自己不舒服是由于被感染还是心理作用,曾数次产生轻生念头。”
病情复发、想哭、孤独感加重,是大家频繁提到的问题。一些药物被耗完的人,开始在头晕、反胃等药物戒断反应里煎熬。
买药按说有几个渠道:如果选择线下门诊,可以请有通行证的代买,带着患者就诊卡到有就诊记录的医院去配药;可以找居委申请配药或开具去医院的通行证;也可以找街道社区卫生中心的精神防治医生。但根据群友们的反馈,因为求助量特别大,居委会的电话很难打通;即使电话打通了,居委会也很难有效率地处理配药需求。社区的卫生中心有些已经关门,去医院则需要出示48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,还要向居委申请通行证——通过的概率并不高。
线上药房也可以开到药。但这其中又有很多问题:一是,患者们常用的平台(京东、阿里药房等)受疫情影响,配送缓慢或者干脆不配送。很多时候,开药申请始终只停留在“你的药品将在X天后通过审核”的步骤。
二是,线上药房只能开到极其有限的药物。我国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根据药物所产生的依赖性和身体危害,将其分为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。盐酸曲唑酮等精一类药相对容易开到,一些线上药房有货。比较难办的是安眠药之类的管制药品——精二药,线上渠道基本很难求到,需要去到线下,而这就又绕回了前面的问题。
林子告诉《中国慈善家》,在熟悉的渠道都走不通的情况下,精神类疾病患者们对新渠道的探索可能比普通人更困难。受病情特性的影响,几次尝试后电话不通畅、求助无回应,很可能在他们身上引发比常人更大的焦虑和失望感。
此外,一些患者不希望公开自己的病情,也很难向周围的人求助。一位进群提供帮助的群友也告诉记者,自救需要稳定的生活环境,如果环境被打破,自救难度会很大。
年轻人尚且能通过互联网做些努力,老年患者则更难自助。群友小千(化名)入群,就是想帮奶奶来求氯硝安定的。“奶奶药要吃完了,甚至尝试过一晚上停药,但是失眠头痛,天天都很焦虑。”她告诉《中国慈善家》,“我尝试过居委配药,但这个要需要在浦东某精卫中心配,他们还没开门。23日尝试过发布求助微博,也求助过亲戚朋友。我还求助了警察,警察依旧让我们求助居委,但居委不肯开通行证。”
不少患者都经历了相似的困境。小千和奶奶还算幸运——她们在最后一刻等到了药。26日,小区附近的卫生院进货,居委成功帮忙配到了氯硝安定。“奶奶本来只剩最后一片了,”她说,“配到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希望。”
缺口不止药品
起初,林子没有求药的经验。群刚刚建起来的时候,基本是靠大家的互助——有患者会在群里分享一些自己成功买到药的途径,还有人会主动加群,把家里余的药分给其他人。
第一步能做的,是把这些渠道信息整合在一起,并慢慢从中筛选最有效的方法。采访时,林子给《中国慈善家》发来了她们整理的开药求助指南,分门别类对应各种需求。这份指南也发在了群里,患者们可以对照自己的需求,选择合适的渠道。
大部分人需要的,是线上就能买到的精一类药物。在快递进不来的情况下,上海本地有存货的医疗平台就成了首选。几个志愿者从群友的经验中锁定了药品比较齐全的“昭阳健康大药房”,并联系到了他们的工作人员。药房的人随后入群,直接和病友对接。群在微博上扩散开之后,嘉会医疗、曜影医疗、曼朗心理等商业诊疗机构联系到了志愿者们,他们同样也加进了群里,对接部分人线上问诊、开处方药的需求。
“这些方法已经可以解决群里大部分的药品需求了。”林子说。
比较难处理的是线下问诊。“今天(27日)我们有遇到一个长宁区的突发状况,是一个女生,除了抑郁症之外,她应该还伴有一些其他疾病。她情况有点紧急了,服了药之后还是全身发抖。她想去长宁那边就医,但我们打了电话,医院是不开门的,更别说能买到药了。”林子告诉《中国慈善家》。
因为之前案例的经验,志愿者给浦东的精神卫生中心打了电话。确认开门之后,林子开始联系自己手里的司机资源,叫了辆可以跨江的车。但是因为当天的核酸报告没能出来,所以只能把就诊时间延迟到第二天下午。林子说,女生目前状况有所缓解。
还有很多建群前大家没有想到过的情况。志愿者小王告诉《中国慈善家》,两天前,有人在群里紧急求助:自己的一位女同事被封在浦东的公司多天,在压抑的环境下和同事起了肢体冲突,情绪涌上来,继而认知障碍、被害妄想病征发作。求助人很着急,问有没有办法帮她买些药?
评估之后,志愿者们觉得当务之急是稳定现场的情况。小王代求助人报了警。信息核实之后,大约半小时,警察到了现场。当时已经是晚上,浦东的精神病医院都已关门,没办法直接就医。后来女生的男友赶到了现场,警察和志愿者们才知道,女生没有公开过自己的病情。
“她家在外地,在上海没有亲人,公司同事和男朋友都不知道她的情况。”小王说,“她可能担心透露自己的患者身份,会被区别对待。”
因为封控,女生最终没能回小区,至今仍和男友暂住在酒店里。
比起其他的弱势群体来说,“被看到”对于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患者有更复杂的意味。美国精神医学学会(APA)的调查研究称,全球超过一半的精神疾病患者没有得到妥当的治疗,除了诊疗水平,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和歧视。很多时候,担心受到区别对待的患者会选择延迟甚至不接受诊治。
互助群里的一位抑郁症患者告诉记者,自己正被封在大学校园里。“身边都是同学,我不希望暴露病情,所以一直在忍耐,但是疫情期间买不到药,很煎熬。”
疫情把一些紧急情况放大并暴露了出来。因为无法问诊和买药,一些患者不得不亮明身份,但是社会可能并没有做好让抑郁症患者站在聚光灯下的准备。
症结待解
十五天里,互助群成了抑郁症患者们的临时港湾。
采访中,一些群友说,除了求药需求,自己当初加群,也是想和大家一起聊聊天,缓解一下孤独感。群里互助的氛围很好,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情绪:“我其实更多地是在群里看大家相互拥抱,像找到了一个共同体。”
林子和朋友们则需要考虑更多。林子说,在群刚建起来的最初几天,几个志愿者到凌晨一两点都不敢睡觉,仔细盯着群里的消息。封控、断药之下,一些求助者情绪低落,有时候会表达些带有抑郁倾向的想法,而这又不免对群内其他人产生影响。有诊所的医生私下提醒林子,群里除了问药的沟通,不建议做其他交流。
志愿者们突然感觉,群聊这个小小的公共空间,并非大家一开始想得那么简单。志愿者八月这样描述她的感觉:“对于一些人来说,这是终于遇到了他能说话的人,大家对他会有共情。但是我发现,这个群是也是有危险性的。”
目前,上海买药的情况在变好。“感觉运力最近有在放开了,像饿了么、美团,有些店已经可以叫跑腿买药了。”小王告诉《中国慈善家》,4月27日下午,她买了一箱矿泉水,运费是12.5元。比起月初那时一单上百的跑腿费,价格已经下来了很多。最近,京东的快递也可以送到她的小区门口了。最初拉群便是为了帮助大家求药,如今,这个目标也变得不那么紧迫了——志愿者们觉得,是时候解散群了。
但疫情还未结束。4月29日,上海卫健委宣布,当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487例,无症状感染者9545例。虽然无症状患者数量已经呈下降趋势,但重症和死亡病例数量曲线已经开始抬头。据八点健闻报道,多位专家表示,上海当下危重症和死亡人数规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。
《中国慈善家》调查了解到,未来一段时间里,管制类药品是否会难配、精确复诊是否有困难等,仍然是抑郁症患者们最关心的问题。另外,解封之后经济状况变差、周围人乃至社会对他们缺乏理解的担忧也多被提出。
林子认为,面向精神类疾病患者的公共求助渠道,在设置时还要多为病人们考虑。目前精卫、疾控等机构发布的就医指引文件,对于群里的这些患者来说,还是过于冗长和复杂了。“长篇大论总是把关键信息都淹没了,”林子说,“这样的指引是没办法帮到患者的,受病情影响,他们没办法读懂复杂的东西。”
另外,医疗资源挤兑的情况下,本就有限的求助渠道更难保持畅通。“上海很多设了急诊的医院,我们之前打过的电话里,起码一半都打不通,有的还没人接,或者是空号。”林子说。
八月则呼吁,既然一些抑郁症患者们不得已在疫情期间公开身份,媒体和公众更应该去关注并尊重这个群体,逐步消解可能的偏见。她觉得,当下就是一个看到并了解弱势群体的契机。
在互助群解散的前夕,《中国慈善家》收集了群内患者们一些想说的话。有的人诚恳地表达了依然挥之不去的痛苦与不安,在混乱之中,他们也在努力疏通自我。
他们写下了这些文字:“精神疾病也是疾病的一种,希望社会不要区别对待。”
“一点点微小的关心和共情都可能有巨大的能量。”
“感谢疫情期间帮助我们的大家。”
还有人简简单单地写了两个字:“加油”。
![绿达之家网[Lvda56.com]](http://cn.lvda56.com/file/upload/202109/06/181134811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