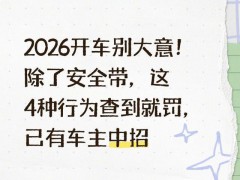随着二胎政策开放,越来越多高龄女性选择追生二胎,她们生下二孩时,一孩已进入青春期,两个孩子相差十几岁甚至二十岁。这种不常见的家庭组合,对每个家庭成员都是全新的挑战,尤其是对一孩来说。面对同胞之间的代际鸿沟,父母被瓜分的注意力,以及突如其来的责任,一孩该如何去适应?

#01
不寻常的手足关系
下午五点,杨安潦草几笔在黑板上留下课后作业,将备课材料塞进背包,匆匆走出教室。双胞胎弟弟妹妹所在的幼儿园下午四点半放学,她已经迟到了半小时,“今天又要被老师翻白眼了”,杨安心想。
到了幼儿园,弟弟妹妹一看见她,立刻从保安亭冲到门口大喊:“姐姐,我饿!”杨安一边讪笑着给老师赔不是,一边把弟弟妹妹的书包挂在手臂上。说起来,这样的生活持续近一年了,但她至今无法适应老师充满责备的眼神。
回家路上,弟弟妹妹不停地和她分享学校里的事情,但她总是走神,这是她每天为数不多的放松时刻,她不想对两个小孩的叽叽喳喳作出回应。回家后,她先给弟弟妹妹安排晚饭,监督他们完成作业,然后才开始自己的备课。
杨安今年21岁,双胞胎弟弟妹妹3岁,大学毕业后,她原本打算去大城市打拼一番,却被父母的请求中断了计划——父亲忙于药店的生意,高龄母亲产后身体虚弱,外婆也病倒了,照顾弟弟妹妹的担子只能由她接下。
有时候,杨安望着弟弟妹妹和她幼时极为相似的脸,感到一阵错愕:“我明明只是姐姐,为什么担负着妈妈的责任?”杨安觉得,自己对弟弟妹妹的感情是复杂的:一方面,他们“绊住”了她远走高飞的脚步;另一方面,她也清楚这不是他们的错。
“如果所有父母在生孩子前,能先假装自己是即将出生的孩子,问问自己是否愿意出生,得到答案再做决定就好了……”杨安时常这样幻想。
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,越来越多中年夫妻选择高龄生子,在这样的家庭,一胎和二胎往往会有较大的年龄差距。这种手足关系不仅会重塑家庭关系,对一胎来说也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。
不同于杨安默默践行着“姐姐的责任”,张帆总是试图逃离这种令她不适应的角色转换。三年前弟弟出生时,张帆已经18岁,一整个暑假,她在家感受到了父母“前所未有的冷落”,从那时起,她便将弟弟视为毁掉自己温馨生活的“元凶”。
“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讨厌弟弟的,甚至可以说是痛恨”,张帆说。她解决这种不满情绪的方式,是故意冷落弟弟。当弟弟吐奶弄脏了衣服,母亲手忙脚乱地擦拭时,她只是在一旁冷眼看着;当弟弟刚学会爬,咿咿呀呀扯她的裤腿,“邀请”她一起玩游戏的时候,她也并不理会。
美国儿童心理学家伯顿·L·怀特(Burton L.White)曾整理出一份《最全二胎“年龄差距”影响对照表》,显示当两个孩子年龄相差6岁以上时,父母往往会更轻松,但一胎却容易心理失衡。年长弟弟16岁的陈浩,与张帆一样,也总是刻意与弟弟保持距离。他将这种疏离视为对母亲的反抗——将母亲对自己的忽视,复刻到弟弟身上。
这种疏离,有时会滑向另一个极端——控制欲。过去十年,陈浩一直将弟弟视为自己军校理想的“继承者”。他曾因为身高与军校失之交臂,一度灰心丧气,转而将这个愿望移交给弟弟,“我大他16岁,懂的肯定比他多啊”。弟弟小时候的服从,一度让陈浩沉浸在这种掌控感中,直到步入青春期后,13岁的弟弟开始反抗:“我为什么一定要上军校?我为什么不能当老师?你只是我哥,不是我爸!”
研究显示,当年龄差异足够大时,一孩通常会表现出一种父母意识,即将弟弟妹妹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。很多年以后,陈浩开始反思自己身上的这种意识,因为这更倾向于控制欲。但对王乐乐来说,这种意识更像是一种“不计回报的母爱”。
自从小自己17岁的弟弟出生以后,王乐乐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放假回家,从小到大,弟弟对她的依恋,总是令她感到快乐。“他很黏我,总是偷偷用妈妈的手机给我打电话,老是问‘姐姐,你啥时候回来’,‘姐姐,我想你了’。’’每次接完弟弟的电话,王乐乐都恨不得立刻冲回家里,一到家就跟外界“失联”了。看着弟弟一天天长大,王乐乐说自己有种“养成的快乐”。她甚至觉得,有了弟弟,自己生不生小孩也不重要了。
#02
被瓜分的偏爱
儿童心理学家佩里克拉斯(Perry Klass)曾说,出于本能,孩子总是在寻找“谁是爸爸妈妈最喜欢的小孩”的证据。因此,父母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多胎家庭的手足关系。
这在王乐乐身上,得到了直观的印证。她认为,自己和弟弟的和谐关系,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父母的公平。弟弟出生以后,父母对她“甚至比以前更贴心了”,那是一种有意维持的平衡——给弟弟买零食时,也会给姐姐买一份;姐姐想出去玩了,也不会把她拴在家里照顾弟弟。
但更多一孩却没有王乐乐的境遇,作为年长的孩子,他们“理所应当”地承担起照顾二孩的责任,被父母要求表现出谦让、包容、体谅等特质。
陈浩用“性情大变”来形容母亲生下弟弟以后的变化,曾经他印象中的母亲是“温柔的、总是笑盈盈的”,但自从有了弟弟,母亲就“总是挑剔我,责备我不带弟弟”。一次,陈浩打游戏入了迷,没有理会在一旁的弟弟,弟弟的嚎哭很快引来母亲,母亲一把将陈浩的键盘摔到地上,愤怒地质问他:“游戏比你弟弟重要?”说完抱着弟弟离开。陈浩心里一颤:“至于吗?”
父母态度的倾斜,一直令陈浩难以释怀。弟弟一岁那年,正赶上他高考,但全家人“好像没人记得这件事”,他独自完成了报考、体检、填志愿等一系列事情,甚至独自面临不理想的分数,而比起这一切,母亲似乎更关心商场打折的奶粉,以及他有没有照顾好弟弟。填报志愿时,陈浩只选那些远离家乡的城市,“想逃得远远的”。
与陈浩一样难以亲近自己弟弟的张帆,也感受到了父母的忽视。“去公园玩的时候,他们只给弟弟买玩具和零食,只顾着逗弟弟开心,而我永远像个外人一样,抱着弟弟的水杯和衣服,不尴不尬地站在一边,也没人搭理我。”
对年龄差距较大的手足关系来说,父母的注意力被瓜分,不仅仅表现在情感上,还包括经济资源的倾斜。
根据《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》,0-17岁城镇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3万元;0-17岁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30万元。并且,从将一个孩子抚养到18 岁的成本和人均GDP的倍数来看,中国的养育成本几乎是全球最高,其中澳大利亚是2.08 倍,法国是2.24倍,德国是3.64倍,美国是4.11倍,中国是6.9倍。在高昂的养育成本面前,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几乎是世界最低。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,绝大部分国家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超过2个,而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低于2个。
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,选择了二胎,就意味着家庭整体生活水平的下降。张帆曾多次体会到这种改变。自从生下弟弟以后,家里原本一年两次的旅游取消了,过去饭桌上的欢声笑语也被关于钱的争吵取代了。以前从不在她面前提钱的母亲,开始频繁抱怨育儿的开销——“奶粉要喝进口的,纸尿裤要穿最好的,现在都流行上双语幼儿园,兴趣班也少不了,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……”张帆想不明白,年近50的父母,拿什么和80后、90后父母比呢?
年长的一孩,早已过了对金钱没有概念的时期,他们能敏锐感知到金钱所触发的竞争。张宇回忆起最初对弟弟产生反感,是因为“他动了我的蛋糕”。弟弟出生前,父母曾向张宇承诺:“你放心,再生一个,你还是我们家大儿子,房子、车、结婚的钱早就给你准备好了,一分不会少你的。”但后来,说好的婚房、婚车都打了水漂,就连结婚场地也从酒店换到了祠堂。如今,张宇已经结婚四年,儿子也三岁了,一家三口仍然挤在出租屋里为凑首付发愁。谈到自己的心结,张宇说:“我不是非要靠他们,是他们承诺了却做不到,我也是他们的孩子啊。”
有时候,经济压力对一孩产生的影响,是以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形式出现。李心就曾是其中的一张骨牌——当她了解到男友还有一个小他21岁的弟弟后,思量再三,决定分手。李心的男友读大三时,他的弟弟出生了,从此男友的学费和生活费全都靠自己赚,他不得不在学习之余兼职打工。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李心不由地担忧:“他父母连退休金都没有,老了以后拿什么供他弟弟上学、结婚呢?如果我和他结婚,这些会不会变成我的责任,这简直是硬生生塞给我一个儿子。”
#03
躲不掉的责任
不同于旁人说走就走的洒脱,身处家庭关系中的一孩,往往无处躲藏。已经成年的一孩,甚至会主动揽下对家庭的责任。
大学刚毕业时,杨安曾想过远走高飞,“只要按时给父母打钱就好了”,她这样想。但很快她就心软了,“总觉得这样是不孝”,让不再年轻的父母独自抚养弟弟妹妹,她做不到。
父母的一次意外怀孕,带来了杨安的双胞胎弟妹。当时召开家庭会议,母亲和杨安都表示反对,“家里已经有两个孩子,再生只会增加家庭压力”。唯有父亲执意要生,并放话说要独自抚养两个新生儿。那一刻,杨安感觉这个责任自己躲不掉了,“他连一个小药店都需要我和妈妈协助,有什么能力做这样的保证呢?”
早已做好心理准备的杨安,对三年后那通匆忙叫回她的电话并不意外。电话里,父母对她说:“外婆病重了,弟弟妹妹还小,家里需要你”。他们甚至积极地帮她在家乡谋求工作,“你可以来离家很近的学校教书”。而电话另一头的杨安,只觉得“自己在往下坠,抬头看,悬崖边站着父母,微笑着向她招手……”
过去一年,杨安每天奔波于学校、药店和家庭之间,有时候会恍惚觉得“回到了忙碌的中学时代”,但不同的是,这一次她“不能以读大学为借口逃避了”。她时常在夜里辗转反侧,回想起17岁的那个夏天,“如果当时自己强烈要求不要留下这两个孩子,父亲还会坚持吗?”但看见弟弟妹妹稚嫩的脸庞,她又觉得自己不应该有这种“罪恶”的想法。
杨安说自己至今仍不打算恋爱,“这是不敢想的,哪个男生会想和一个整天追着孩子喂饭、根本没时间约会的姐姐谈恋爱呢?”“弟妹还有20年才能自立,到时候我40岁,爸妈65岁。这20年是我人生最好的20年,却注定要拖着我的家庭沉重地走。”
而对弟弟才4岁、父亲已经50岁的张帆来说,虽然理性上意识到姐姐对弟弟负有法律上的抚养责任,但她目前并不想面对, “现在不想养,说不定以后会想通。”
![绿达之家网[Lvda56.com]](http://cn.lvda56.com/file/upload/202109/06/181134811.jpg)